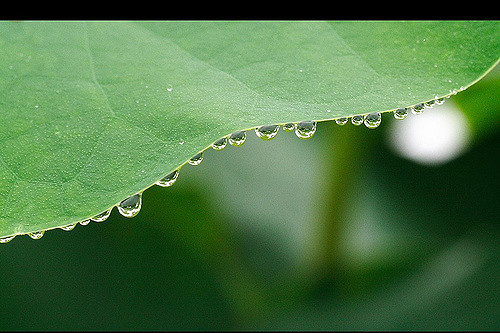我的研究之路與性別省思
by 林昭吟
成長背景
我父親生於福建省泉州,祖父母務農。父親曾經參加過中國的8年對日抗戰,戰爭過後返回家鄉開始從事船運的農產品貿易,將大陸的農產品用船運輸到淡水或高雄販賣,因此經常往來於福建與台灣之間。 我母親是澎湖縣馬公人,8歲時隨家人遷徙到高雄市。母親就像台灣版的「阿信」一樣,8歲時就得照顧滿周歲的姪女(她大姊的女兒),一早起來要生火煮飯,煮好飯後,就一路狂奔到學校上課。有時,擔心背著的姪女哭聲吵到同學,就站在教室外上課。14歲時,開始到文具行當店員賺錢貼補家用。22歲時,為了躲避婚姻,她應徵了日本軍隊徵召的護士工作,到香港的日軍醫院工作了3年才回到台灣。二次大戰結束,父母已雙亡,受著我大姨的壓迫,嫁了當時從事海峽兩岸貿易的父親。大陸淪陷之後,父親在福建的家產及貨輪全都被共產黨沒收,而在台灣的經商又屢遭失敗,母親才不得不又回到職場,在高雄楠梓加工區的一家日本電子公司當翻譯,一直到60歲才退休。

我出生於高雄市旗津區,家中六個女孩,一個男孩,我排行老六。父親經常在外,家中由母親掌管。母親對我的影響很深遠,不僅是在性格上的遺傳,更有她自己以身作則的潛移默化。母親是個不多話的人,做事敏捷、頭腦清晰。在我兒時的印象,我們的互動中很少有談心事的情況,往往在簡短的言語中就知道彼此的心意。母親雖然接受了日式教育,有著強烈的傳統禮教及道德思想,但她嚮往的卻是西方開放式的教育與民主自由的制度。因此,對我們小孩的管教是極其民主的,總是一視同仁地對待我們,從不表現出特別溺愛誰,並從小尊重我們的意願,不強迫我們念書。九年的國民教育之後,不論我們選擇就讀職業學校或普通高中,她都支持。家中只有我與大哥喜愛念書,母親就盡力幫我們籌學費。我當時出國留學的機票錢,還是母親拿部分退休金資助的。母親晚年白髮蒼蒼卻掩不住她堅毅而美麗的氣質。我會選擇物理系為第一志願,應是來自於母親的遺傳。
研究之路
我於1981年畢業於淡江大學物理系,留在學校當了四年助教後,獲得了美國扶輪社的交換學生獎助金出國念書。1989年獲得了美國威奇塔州立大學的物理碩士,我的論文指導教授為著名的華裔低溫物理學家何健民博士。一年之後我搬到德州,在休斯頓大學攻讀物理博士,從師於朱經武教授(為美國科學院及台灣中研院院士)研究高壓下高溫超導體的物理特性,藉以探究發生高溫超導的機制。1993年11月獲得休斯頓大學的物理博士,並在德州超導研究中心作短期的博士後研究工作。於1994年3月底從美國返回台灣,在台灣大學物理系黃昭淵教授的指導下擔任博士後研究。黃教授是台灣大學凝態科學中心的開創者,1996年聘我為凝態中心的助理研究員,並和他一起建立「磁電材料物理」實驗室。我在2005年和從美國貝爾實驗室回來的陳正弦博士(第三任的凝態中心主任)共同執行國科會的國家型奈米計畫「自旋電子材料中微結構和其相關磁性及傳輸特性之研究」,建立了脈衝雷射濺鍍系統,開始製作薄膜異質結構,遂將我的實驗室重新命名為「尖端薄膜異質結構及自旋電子」實驗室。回顧自己在20年的研究工作中,秉持的一貫信念是追求物質界的真理,正如在人生中也是不斷尋求自我實現一般。研究中經過省思,體認到「學術卓越」若無法轉化成能量來提昇台灣社會的競爭力,它只不過是個高尚的價值觀而已。因此,思考著如何將新知識與現有技術結合,用非常有限的研究經費培育出具有創新性的科技人才。2012年我的實驗室成功地整合了新穎薄膜的成長與自旋電子共振技術,發表了全世界第一篇運用鑭錳氧半金屬作為自旋幫浦的研究群(見2013 IEEE. Tran. Mag.中Axel Hoffmann的評論文章)。在訓練研究生的過程中,我自己也深深體會到教學相長的樂趣。

性別省思之路
1999年在第23屆的世界純粹物理與應用物理聯盟(International Union of Pure and Applied Physics; IUPAP)大會會議中,有鑑於女性物理學生及研究學者的比例遠低於人口的性別比例,會議的決議書中建議所有會員國成立女性物理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Women in Physics; WGWIP),以增加女性物理學生及研究學者的比例為目標。因此身為IUPAP團體會員的台灣物理學會也開始推動相關事務,並於2000年的物理年會(台灣大學主辦),決議成立物理學會的女性工作小組。戴明鳳教授(當時在中正大學任職現已轉任清華大學)被選為小組召集人,會議中並決定組團代表台灣參加第一屆IUPAP在巴黎舉辦的女性物理學者研討會,我亦是被邀請的團員之一。我因為參加了此研討會,才開始注意到職場的性別差異,並積極參與相關的活動。女性工作小組在2003年正式編制為物理學會下的女性工作委員會。由台灣大學凝態科學中心的林麗瓊博士擔任召集人,我為副召集人。圖四為第一屆女物理人研討會的合影。我於2006及2007擔任該委員會的第三任召集人,在任內舉辦了第一屆的物理人挑戰研討會及第一屆女科技人研討會。我卸任後由成功大學的鄭靜教授擔任召集人,並一起組團參加了第三屆IUPAP在韓國首爾舉辦的女性物理學者研討會。也因為我們積極的參與,台灣團隊已經被肯定為推動有功的工作小組,我亦被邀請在會中進行一場演講。
2006年我及其他來自不同領域的四位教授共同主持一個國科會(現今的科技部)的計畫「性別與科技規劃推動計畫」。此計畫的目的在於提升女性在科技界的網絡及能見度,以及建立一個性別資料庫。我們也殷切期盼藉著執行這個計畫,形成一股推動力,能夠讓國科會正視科技界的性別差距,而願意投入更多的資源去做長遠制度性的規劃,使得優秀的女性在科技專業奉獻長才之餘,亦能與伴侶攜手共同建立家庭,為國家社會生養培育更優秀的下一代。也因為執行了兩個三年計畫,我們集聚了一股力量,在2012年成立了台灣女科技人學會。此學會的成員至今約150位,包含了理工各科系的研究學者及學生。
我是個崇尚自由的人,覺得女性不選擇物理或女性選擇家庭而不選擇事業是基於個人自由。但是,參與女物理人推動的幾年經歷下來,我才理解這些問題與人權問題有關。女性有沒有受到不平等待遇,是人權有沒有被伸張的問題。而女性物理人有沒有受到國科會、學術單位或學校不平等的待遇,也是人權問題。同樣的,如果男性學者有受到不公平待遇,也應該加以申訴。只是,傳統的台灣社會以男權為主,女性普遍在社會、文化的影響下,大多逆來順受,較少爭取利益。受到不公平待遇時,也習以為常。在物理界裡,大多數的男性物理學者無法親身體認到女性物理學者在工作職場上身為少數人的感受。
我開始認真思考同性戀的問題始於2012年。那年12月我在美國聖荷西執行國科會的「前龍門計畫」。我向一戶美國家庭租了一個房間,屋主夫婦把我當家人般無所不談。我在與他/她們相處的兩個月中,重新認識了美國中產階級的價值觀,並體會到他/她們對美國現況的種種不安,包括「性別認同」這件事。因為屋主的三女兒蘇茜有這個問題。由於她母親從小成長於天主教背景,對道德規範特別嚴謹,故常為此事憂鬱。 蘇茜年約20歲,應是念大學的年齡卻輟學在家。原因是她有男性追求者,亦有女性追求者,自己無法從中取捨,故在兩邊徬徨,進而無法過一般大學生的生活。我觀察的結論是她的女性追求者在性格上是剛烈的,是叛逆性強的,和蘇茜的個性恰好相反,所以蘇茜受到吸引。加州是美國有明確法令保障多元性別人士的四州之一,同性戀是被認同的。然而家人不斷地反對,讓蘇茜常常在內心掙扎。這樣的矛盾在這個家庭裡產生了許多的壓抑、憤怒及悲傷。傳統性別的定義,乃是從生理的差異來判斷,人類和動物一般具有某些性特徵後,根據性特徵被定義成某性別。在另一方面,人類的文明發展到一個地步,繁衍種族已經不再是生存目的。因此,部分人的性別,開始由生理的特徵轉向心理的特徵。若衛道人士或保守的父母無法認識到這點,社會永遠無法達成和諧,家庭悲劇也會持續發生。
結語
女性擁有很多的特質是非常美好的, 尤其女性的敏感與愛心是上帝給人類最好的禮物。我無法想像人類的社會沒有了這兩樣特質會是怎樣?雖然說學理工科的女性往往較之於非理工科的女性更為理性些,但敏感與愛心的特質卻是依然存在的。學理工科的女性也較為獨立,因此容易成為單身貴族,但我極其相信也期待,未來的台灣社會能發展成真正男女共治的社會。也就是說男女皆能基於個人的本性發展專長或專業, 而不是基於傳統的觀念:男生該怎樣、女生該怎樣。這不但需要父母及教師的覺醒,也需要政府在制度上及教育上的設置。但我也不願看到另一個極端:忽視兩性的差異或否認兩性同在的必要性。人類要永續發展,一定要遵守大自然的規律。
(林昭吟,1981年淡江大學物理系畢業、1987年美國維奇塔州立大學物理碩士、1993年美國休斯頓大學物理博士。曾任美國德州超導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台灣大學物理系博士後研究員、美國IBM-Almaden研究中心訪問學者。研究專長:超導及磁性氧化物薄膜、自旋電子物理學。重要學術服務包括國際期刊 J. of Magnetism and Magnetic Materials 及 Scientific Report 編輯委員、台灣磁性技術學會常務理事、台灣中子科學學會副理事長、中華民國物理學會女性工作委員會召集人、台灣女科技人學會副理事長等。本文轉載自《女科技人的理性與感性》P.68-75)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