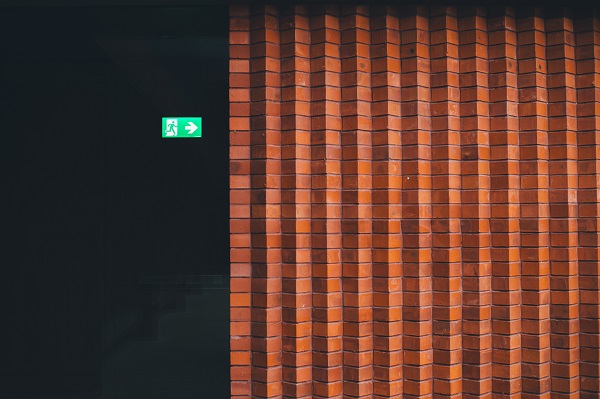婚姻中的在地抗爭─專訪蘇芊玲
by 胡淑雯
有沒有「女性主義婚姻」?什麼是「女性主義婚姻」?
在婚姻面前,女人不戰而敗;若選擇奮力相搏,就要準備花一百分的力氣得兩分成果。
婚姻,對女人來說,終究是十分辛苦的,即便是我,仍然會用「困境」這個字眼來描述自己在其間的努力和掙扎。小到逢年過節哪一次哪幾天要回誰的家過,大到(相當程度上連自己都內化了的)將對方生涯擺在優位的傾向,以及,與夫家人同住相處時常常不由自主引發的焦躁感(聽到有人在廚房忙就緊張起來,飯後考慮是不是該去洗碗碟,是不是不該在外面待得太晚……),近二十年的婚姻下來,替自己解毒的功夫,可以說沒有一刻停下來。相對地,對方就不必經歷這些。無論他是一個如何具備人道修養、尊重異己的人,我們所身處的位置就是不同,做為男人,他背後所有的支撐就是不一樣。
但比起其他女人,特別是上一輩的女人,我很清楚自己已經站在比較好的婚姻條件中。在個人的層次上,我很明瞭自己的能動性與對自我的堅持是不可多得的;我的家庭以及我求學的過程都為我保留了這個空間。
我自小就野,自我意識很強,從不害怕抗爭,帶著這種性格進入戀愛與婚姻,我從不以扼殺自我的方式來交換感情,以至婚後至今,我對婚姻生活的情緒感受一直都還蠻正面的。此外,我的伴侶也算得上難能可貴。
他的人道、善良,對我的全然接受,對我朋友的大度與尊重,是我很看重的;而他個人對我的喜歡、欣賞,使他願意在婚後儘可能開放空間任我發展,因為他無論如何也不願冒險失去我。
我能夠在結了婚的狀況下做那麼多事,得到如此的空間,雖然我的堅持和努力是主要因素,但仍有相當的部份是建立在對方對自己的感情上。這顯然不完全符合所謂女性主義的抗爭模式。
我所想像的「女性主義婚姻」,應該是婚姻關係中的雙方都深具性別意識,瞭解性別體制與文化賦與男性的優勢,深刻地思考反省並試圖改變。我和伴侶間靠的比較是感情,換了另一個人就不一定是現下的景況了。
他或許能夠瞭解、同意父權體制的壓迫性,但對性別政治並未有特別的看法,對性別解放運動也沒有強烈的參與企圖或認同感(而比較接近「我了解,但我無能為力」的態度),所以,我並不認為發生在我們之間的是所謂「女性主義式婚姻」。
話說回來,雖然有愈來愈多男性有能力操作女性主義的語言,以性別的觀點來分析各種社會現象與婚姻制度,但我很懷疑自己的婚姻裡需不需要這種男人。
如果他們只是在知識與概念的層次上掌握了女性主義,而不在生活中實踐,女性主義便不過是他們拿來賣乖或耍炫的工具,甚至以此向身邊的女人進行不合理的索求(妳有了我這樣的「新好男人」,還有什麼不滿足?!),陷她們於更不義的處境。
我認為,一個人具不具備性別意識與他懂不懂得操作這套語言並不等同,我的伴侶雖然不會使用女性主義的語言,卻也是粗具性別意識的人(至少他選擇了我這樣的一個人)。這樣也許也不錯,否則,要時時刻刻破解對方聰明的表態、頭頭是道的辯詞,陷入那種「比功力」的情境中,想來也挺累人的;萬一老輸給他,豈不是在意識上也受到壓迫。
有人會問:「女性主義者為什麼不離婚?」對於我這樣的女性主義者來說,婚姻所以能夠持續,正因為我絲毫不懼怕變動。
拿「外遇」這個人見人誅的例子來說,當婚姻關係中的任一方或雙方向外發展了其他的關係,在我看來,除了為兩人的關係帶來遺憾、傷心之外,總還有些正面的東西。(例如促使我們思考:原來對方還有熱情,原來對方的情感和身體還沒有死去;她/他其實需要的是什麼,我怕失去什麼;原來婚姻只是人生的一部份和一個階段;我們在一起的幸福是什麼,各自沒有活出的人生又是什麼……)
如果兩個人的空間是開放的,選擇是自由的,婚姻關係中的所謂「不穩定性」便是必然的,要欣然接受甚至享受的。婚姻的「女性主義指數」,我想,其中重要的元素之一便是這種「不穩定性」。
說來吊詭,愈是不害怕變動、不害怕外遇、不害怕離婚……,反而愈能造就婚姻關係的吸引力;愈是害怕離開婚姻,老覺得自己沒有對方會活不下去,就愈對婚姻、對兩個人的關係有害。
婦運的能量應轉向創造不婚女人幸福的可能
如果說,施寄青、李元貞等婦運前輩是在比我們這一輩更缺乏支撐力量的情況下,在自我與婚姻兩相權衡下,不得不做離婚這樣的抉擇,我的狀況可以說是站在她們奮力累積的婦運成果上嘗試在婚姻中走不同的路,營造能夠運轉下去的、遠離權力壓迫的婚姻關係。
施與李的經驗和選擇對女人來說,是深具啟發意義的,她們教會了女人:當婚姻與妳的自我發生根本的衝突時,不必然只有一條路,妳其實不必磨滅自我委屈地留在婚姻中。
循著這個脈絡往下看,現在頗為活躍的年輕女性主義者,走的是一條與我們更不一樣的路。她們多數在校園中便接觸了女性主義,認同婦運;二十歲左右便學會堅持自我,並且為自己搭建了強烈的女性主義意識。她們對維繫父權運作的各種機制,尤其是婚姻制度,抱持強烈批判的態度,也因此,她們無論如何不會輕易走入婚姻。除非我們的社會文化土壤能夠培養創造出在意識上氣質上相對的男性,否則,對這些年輕的女性主義者來說,再愛對方都不值得進婚姻裡去混一遭。
有些時候我會深深感慨,這種頭腦先於身體、先於生活的醒悟,不一定使人比較快樂。問題倒不出在這些年輕女性覺醒得早,問題在於,婚姻之外的其他可能性沒有足夠的空間與資源被成熟多樣地開發出來。例如同居、單身、不婚、外遇、女同性戀等脫逸於傳統婚姻的生活選擇,許多至今仍止於某種粗具輪廓、簡單浪漫的認同,未發展主體與經驗的細節。
女性主義者花了很多力氣重新思考婚姻,花了很多力氣去透視、拆解其中的權力與控制;女性主義者看透了婚姻,因此鼓勵自己和其他女人別再輕易往裡跳,但是,我們可不可能在拆掉舊的惡之後,進一步給覺醒了的女人一個能夠存活下去,甚至充滿滋養的前景?否則,個人的寂寞仍將找不到指向,個人的痛苦也還會繼續。
也許,時候到了,我們應該將火力落實為細緻的主體和經驗的重建,為女人的另類生活及其幸福快樂的可能營造溫床。
期待更細緻與複雜的女性主義婦運
通常,我不太用女性主義的語言和朋友進行生活上的對話,也不喜歡用女性主義的概念自行為她們的經驗命名,因為我能夠深切瞭解並體會我們文化中女人身處的困境,包括我自己也還在某種困境與解困的過程中,所以,我不喜歡批判女人的經驗,論斷女人的是非。也許,朋友們喜歡找我談心,正因為我總是先擁抱了她們的經驗;我緊守感情這條線以保留對話的空間,而不急於將概念或真理信條塞入她們腦中,對朋友如此,對女兒、對學生,也是如此。
自己究竟有沒有受到壓迫,在親密關係裡絕對騙不了自己。如果我的朋友因為渴望一份長遠而穩定的感情而選擇了結婚這條路,我會在寄予祝福的同時,叮嚀她無論如何別將壓迫美名。
我很鼓勵女人去面對自己心裡、身體裡,其實不太一樣的、蠢蠢欲動的東西,或者感覺不舒服、委屈,沒有受到尊重的部份。我想,這些正是女人面對了之後能夠蓄發出能量的東西。假以時日,等個人將身處的情境搞清楚,價值觀也確立後,我會支持她所做的任何決定。
除了針對大環境進行撻伐的功夫,我十分堅持女性主義必須肯定生活中的女人。改革的力量不在別處,就在這裡。
我從不鼓勵女人為了「政治正確」去做勉強自己的事,包括勉強離婚。如果求全而復生很難,那麼這個求全沒有意義。
我想,沒有任何一種選擇比另外一種選擇更輕易或更困難。選擇進入婚姻,留在裡面,或選擇離開,甚至根本不進去,分別都需要某些獨特的勇氣和條件。選擇在裡面,活下去,所謂「在地抗爭」,不見得是一條沒有進展的路,重要的是,我們要尊重每個不同女人的生命情境與價值觀,給不同的女人實踐的空間。
決裂的、革命的、是非分明的論述與行動號召自有其迷人、撼動人心的力量,但我並不太相信生命可以那麼分明絕對,因此我更期待女性主義婦運的複雜化與細緻化。唯有如此,婦運對人性、對個人處境的體會與掌握才可能更進一層,更貼近群眾的情感,也才能在運動上走出深度。
(本文原載於1996年10月《騷動》第2期,轉載自蘇芊玲著作《我的母職實踐》,蘇現為台灣性別平等教育協會理事長)
(感謝本文由女書文化慨允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