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本見證迫害猶太人歷史的少女日記
by 黃淑怡
Ik weet wat ik wil,
我知道我想要甚麼
heb een doel,
我有目標
heb een mening,
我有想法
heb een geloof,
我有信仰
en een liefde.
我有愛
(1944年4月11日星期二)
1945年1月27日是在人類歷史上是一個解放的歷史,當俄軍走入奧許維茲集中營(Auschwitz-Birkenau)時,他們並不明白在冰封的波蘭白色大地下,有多少猶太人正骨瘦如柴飢寒交迫病入膏肓的等待戰爭的結束與自由的到來,而這個集中營僅是德國納粹迫害監禁猶太人數個集中營最主要佔地面積最大的一個而已。戰後德國將這一天,定為納粹受害者紀念日,世界各地也皆有相關的紀念活動。荷蘭在德國納粹佔領的期間,粗估計90%猶太人受迫害而喪生,年幼的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也是其中之一,在她短短15年的人生裡卻留下了一本日記,記載這段殘酷無情血腥且泯滅人性的歷史真相。今年是位於阿姆斯特丹的安妮法蘭克博物館50週年紀念日,即將於今年4月卸任的荷蘭女王也在1月27日這天為新展區揭幕,警惕世人永不忘自由的珍貴與戰爭的教訓,筆者有幸在留學期間親臨新翻修的博物館做第一手觀察。
二戰至今,有許多當年受害者的口述歷史、戰爭文學、考證歷史學或經濟政治學研究納粹加害與猶太迫害史,本文要以女性(陰性)書寫的角度來切入安妮日記與該博物館(註:為了尊重原著,日記節錄以荷蘭文呈現)。
安妮一家本住在德國,她的父親奧圖‧法蘭克(Otto Frank)在1933年感受到希特勒執政後的德國開始進行一連串反猶太的言論與政策,於是決定舉家搬遷至荷蘭並開始了醬汁生意。安妮博物館的現址263 Prinsengracht、Amsterdam便是當年奧圖‧法蘭克的生產工廠與倉庫。移居荷蘭的前幾年安妮和姐姐在這裡與一般人一起上中學,直到1940年5月後,德軍占領荷蘭後隨即實施管制猶太人政策,猶太人必須只能到猶太學校上課,猶太人不能搭電車,猶太人必須佩帶黃色星星,猶太人只能在下午三點到五點出門買東西,猶太人不能溜冰,許多餐廳和公共場所也開始貼出禁止猶太人進入(Voor Joden verboden)的告示牌。當時猶太人幾乎已經到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處境,1942年7月6號奧圖‧法蘭克決定要帶著全家人,包含妻子與兩位女兒與其他四位友人躲在工廠後方的加蓋部份。整整兩年,這八個人過著不見天日像坐牢般的生活,沒有隱私,食物短缺,他們的性命全都維繫在奧圖‧法蘭克的四名員工手上。安妮的日記便是在這兩年的躲藏歲月中誕生。
一開始安妮只是片段零星著書寫,直到1943年,她從收音機聽到當時被驅逐至英國的荷蘭首相在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上對全荷蘭人呼籲,要大家保留日記和照片作為日後戰爭結束之後的見證和證據,於是安妮在被捕前的短短七個月重新翻修日記並更大量的寫作,直到被捕前的兩天(1944年8月1日)。對於一個13歲的少女,生活本應可以自由的玩樂,騎腳踏車感受微風清拂、談戀愛,這場肇始於男性獨裁者野心與極端的種族偏見主義,最後演化成以國家之名手握兵權和軍事科技力量,把這樣花樣年華、情竇初開的女孩,逼進了密室中。安妮沒有如吳爾芙之幸運享有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won),她必須與一個素未謀面的成年男性共躲一室,沒有隱私,物資缺乏且行動受限,走路要輕聲,盡量避免說話,連上廁所都不可以沖水,以防任何聲音被兩旁的鄰居或樓下的工人聽到。
Overdag morgen onze gordijnen nooit één centimeter opzij
白晝時,不能打開窗簾,連一英吋都不行(1943年11月48星期六)
年輕的她不解政治的無情,戰爭的殘暴。她憤怒、她怨歎,她每每問上帝猶太人到底做錯了什麼?但她選擇相信上帝的安排。她只能透過窗簾的縫隙窺探外界,從閣樓的小窗望著外頭的飛鳥羨慕而興嘆。然而她始終心懷希望,相信戰爭終會結束,自由一定到來。除了長安妮三歲的姐姐之外,安妮沒有同儕,於是她將最私密的日記當作唯一可以傾訴的對象。絕大多數文章皆以擬人化,親愛的凱蒂(Lieve Kitty)開頭,唯有創造一個幻想的朋友,她才能揭露內心最深處的感受和情緒。她在這幽閉的密室中長成一個有自信的女孩,她靈敏的心思感受到其他七人的情緒轉化,而她也更覺察自己發展出多重面向的個性。在博物館中,一段安妮父親的談話,也顯示奧圖‧法蘭克在戰後首度閱讀女兒的日記發現這個女兒如此的陌生,他跟她朝夕相處,卻從未發現自己女兒在那段絕望日子中,是這麼充滿熱情與希望與忿恨。

參觀博物館對筆者來說是一個很沈重的經驗,當我越往後頭走,開始進入所謂的Het Achterhuis(祕密後房)那昏黃的燈泡,狹窄的甬道,陡斜的樓梯和空無一物僅剩牆上安妮張貼著當時明星的小像與繪畫。原本是客廳的牆上還保留著安妮與姐姐長高的紀錄,緊閉的門窗,不透光的黑色窗簾,兩年、整整兩年,兩個家庭8個人生活在不到20坪的加蓋密室是何種日子。奧圖‧法蘭克是這八個人之中唯一活下來的倖存者,1960年當他把這裡改建成博物館時,他堅持裡頭要空無一物,除了那個用來掩飾的活動書櫃和書架上的書之外,因為他要世人瞭解,許多猶太家庭在戰爭之後,迎接他們的就是這種親人朋友家人不會再團聚的空虛寂寞孤獨與空白。參觀完建築本體之後,博物館的動線會引導遊客至隔壁的展覽廳。那裡以昏黃的燈光陳列著八個半透明的壓克力照片。每張照片底下是一張泛黃的檔案卡,上面以舊式打字記載著這八個人進集中營之前的資料,姓名、生日、藏匿地址。背後是當時他們被發現時的照片或被捕前進入集中營的照片。走到安妮的部分,一開始我並未發現安妮的壓克力板背後是一個小螢幕,後來等螢幕再度發亮,我和另一名西班牙籍的媽媽,分兩旁斜站,仔細盯著螢幕,那是一個英軍的紀錄片,約莫40秒,那是英軍解放伯根貝爾森集中營(Bergen-Belsen)所拍攝的黑白影片。小小的安妮和姐姐就在那一堆堆女孩的屍體中,或仰或趴,赤腳,其中一個小女孩的內褲還被拉至大腿。安妮並未能生存下來,她在解放前七天死於斑疹傷寒,屍體像垃圾一樣被堆棄曝屍雪地。影片結束後,我與那位母親同聲吐氣。震驚、感傷與對於人性的黑暗,不需要翻譯。戰爭結束了,但歧視並未消失,當初的受害者,如今演變成加害者不斷以軍事武力壓迫與侵占鄰居的土地。居住在世界上的人類並未和平相處尊重以待。許多地方內戰仍頻,針對種族、宗教、性別、性傾向、身心障礙、年齡、外表胖瘦的歧視,乃至於對動物的虐待。偏見、歧視與迫害透過政治與國家機器和不開放的人心仍舊繼續存在。
Eens zal deze verschrikkelijke oorlog toch wel aflopen, eens zullen wij toch weer mensen en niet allen jodenzijn!
有天這個糟糕的戰爭一定會結束,到那天我們將再度成為一般人而不僅是猶太人(1944年4月11日星期二)
相關連結
閱讀淑怡更多的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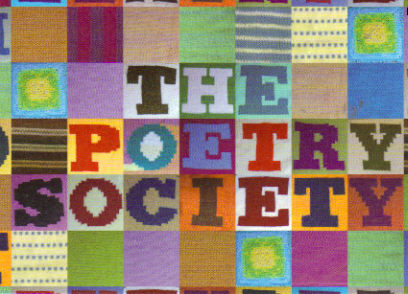
那一年我也讀過詩



